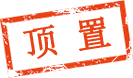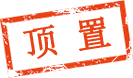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无脚蛇 于 2025-9-4 09:46 编辑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海丰县海城镇南门社区的南门红色文化街,正通过“红色热土,英雄人民”主题专栏,静静讲述着海丰人民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立后那段段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程。


“抗日战争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护送何香凝、柳亚子史料馆”里清晰记载: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中,从香港、惠州、澳门到海丰、龙川老隆再至韶关,处处可见海丰革命者、交通员、爱国商人与革命群众奔波的身影。他们以大义凛然的担当与奉献,用血肉之躯诠释了民族危亡时刻的赤子之心。
史料馆内,抗日老战士的回忆实录与抗日战争红色故事缓缓铺陈,将海丰人民在营救香港文化名人过程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娓娓道来。
抗日老战士的回忆实录 护送何香凝柳亚子 袁 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进攻香港。二十五日港英总督杨慕奇向日军投降。
十二月下旬周恩来同志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在香港之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转移到后方。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经过三个多月紧张工作,克服许多困难、险阻,在香港日军严密统治下,抢救出进步文化人及民主人士七、八百余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
驻港八路军办事处谢一超同志接受廖承志、连贯同志的指示,担负护送何香凝、柳亚子及其家属前往海丰的任务。他在港联系好我方机航船,分别护载他们离港。当时,为便于作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何香凝老人准备公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保护,故由谢一超同志护送在海丰县汕尾上岸。柳亚子及其女儿柳无垢由谢一超同志爱人护送,走红草马鬃这条线。可是船开至大鹏海面,突遇海贼截劫,一超同志与匪周旋了几天,孤胆应付。后匪方始放行,终于四二年一月中旬安抵海丰县马鬃。这批爱国人士分别由地下党组织安排到不同的地方隐蔽。

何老太太及其儿媳妇经普椿同志从汕尾直达海城后,何老太太向国民党军队驻海丰保安二团团长邓龙启提出保护,邓龙启碍于何老太太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让她住在自己的公馆(干园,即朱厝祖祠)。何老太太的儿媳妇则不公开身份。据回忆,当时她怀着孕,住在东门头“春利旅店”(即现红城酒楼)。谢一超同志住在我家,他化装成何老太太的义儿,经常出入于干园和春利旅店。作为何老太太婆媳的联系人。
何香凝同志到海丰后曾在红场召开民众大会,宣传抗日救亡。另一次借宗姓关系到小汾村(廖姓村庄)拜访,召集农民宣传抗日救亡。她老人家不懈地做抗日的宣传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不安。因此,国民党当局匆忙地送她走了。临走前,她老人家画一幅“威震群峦”的老虎和一幅“凌霜怒放”的菊花,分别送给我和一超同志(赠给我的画和柳亚子先生赠给我的联,文革期间被抄家时,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也给小汾村廖姓赠画一幅。
当时柳亚子的身份不能公开,汕尾是交通枢纽,汉奸、特务麇集,马鬃是个小地方,穷乡僻壤,特务没有注意。所以柳亚子先生的船选择在马鬃靠岸,由地下党安排柳先生扮成们黄姓大商客,到马鬃与红草交界处的“新村杨”,在港商杨胜昌的大院,住了十多天。后恐久住不妥,于农历十月下旬,由一超同志护送到联安下许村。春节前一天,再由地下党南路支部负责人郑耀同志护送到公平日中圩附近村庄,由钟娘永同志(是当时我党打入国民党里,当伪乡长的地下党员)负责掩护安置。柳亚子赠我的诗中有这样几句:“将迎难忘日中墟,直到兴宁分手初。况瘁钟郎情谊重,飘潇谢嫂讯音虚。沧桑历劫还逢汝,恩怨填胸孰起余?安得梓乡成解放?彭生墓上见旌旗。”。钟郎说的就是钟娘永同志,谢嫂就是谢一超同志的爱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钟娘永同志掩护同志的责任心和高度热情。

四二年二月底,我接蓝训材同志指示,要我筹备足旅费(约人民币二千余元)协助护送柳亚子先生父女。二月廿九日我们一行五人(一超、蓝训材、柳亚子及其女儿)从日中圩出发。柳老父女坐轿,我们三人步行。第一天到陆丰县新田,住在米町岗小旅店。第二天到河婆圩,这天到达较早,柳老女儿柳无垢提出不坐轿,要步行。我们到圩内找了一双冯强胶鞋,比她的脚还长两指多。她再用针线把鞋子缀小,在城里生活惯了的姑娘,穿着不合脚的鞋子,走起路来一歪一扭,逗得大家都笑了。从河婆到安流(五华)有九十华里,又要爬几座高山,途中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还是说服她坐轿。但这时她那双脚已是打了不少血泡了。三月三日,天刚亮,我们就起程,由蓝训材同志带路,向黄岗七斜径进发。约十点钟,我们将要翻越七斜径时,山峡里,突然出现十几个身穿黑衣,手执驳壳枪的人,用客家话命令我们站住,不许动,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既怕遇上特务,又怕路费被抢,心里忐忑不安。这时只见一超同志挺身而出,很镇静地一招手,请求见他们的头目。一超同志约摸去了两个钟头就回来了。他站在一块大石上与一个身穿黑衣、手执驳壳枪的人握手道别,其余拦路的都撤走了。我们继续上路时,就从那个身穿黑衣服的人下边走过,他站着的姿势,好象在保护我们过关。至此,我深深地佩服一超同志的智慧和勇敢。事后,我曾问起此事个中奥妙,一超同志总之笑而不答。
到达安流时,已是日头下山了,蓝训材同志找到盐运站叶振成同志。叶同志安排我们吃饭,并找到往五华城(转水)的木帆船。饭后我们就在木帆船过夜。从安流到五华城转水,因水浅又逆流,我们往往要停船铲沙开路,三天才到达。蓝训材同志不便与我们同路,因过去曾以染衣匠身份在这一带活动过,所以自己一人步行小路到老隆,而我们四人则搭车前往老隆。

三月十日左右,晚上,我们安顿在谷行街一家小旅店住宿。我与一超兄住一房,柳老父女住一房,表面上我们互不相识,以防不测。当晚训材同志即派人来联系,告诉我们粤北省委受破坏后,地下党组织已撤退,无法接交,新的接交地点,尚待寻找,要我们住下来等待联络。这几天大家心情异常焦虑,真是度日如年,怕夜长梦多。但到了第四天,蓝训材同志即派人来通知,要我们转交给兴宁地下党。三月十五日下午,我们四人搭车赴兴宁。因当时汽车缺油,用木炭烧火代汽油,走得很慢。下午五时才到五华属的陈店车站,只好停下来过夜。当晚半夜,伪警到旅店查房,将一超同志带走,我很紧张,怕问题暴露,
又不敢同柳老父女商量。幸好ー个多小时后,一超同志安然返来。原来是一超兄在旅店登记本上的年龄与答复伪警盘问时的年龄有一岁之差,引起了怀疑所致,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清早起床,乘车往兴宁,因兴宁国民党大官多,恐被发现有所不便,故在车站停下来研究对策时,蓝训材和黎约仑已在车站等待我们。后经谢、蓝等决定柳老不住大旅店,但亦不好住小的。一超同志让我和黎约仑先进兴宁城找较合适的中等旅店。
在兴田路旅店集中处,查勘了安多尼旅店,认为比较合适,报谢等考虑后同意,我再去定了房子,住宿手续由柳亚子先生亲自办理。我与一超兄另找一间与安多尼旅店相隔几间的华隆小旅店住下。一超同志在房里盘旋了几圈,然后写了一封信,让我到兴宁银行电台找何××(名字忘记了,是电台台长)约他到华隆隔壁的茶楼与一超同志见面。与何同志联系上以后,通过电台与在韶关的何香凝老人通了话,并通过何同志与兴宁地下党取得联系。第三天,柳亚子先生父女就被兴宁地下党同志接往石马乡。在转接前夜,柳老叫我买了三张宣纸和笔墨,翌晨临别时他将写好的三付中堂(七律诗)赠给我们(谢、蓝、袁)。给他们两人的诗我已忘记,赠我的是:“赠我延年之大药,感君援手在穷途”。

至此,我们总算顺利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护送任务。
四二年三月,我们护送柳亚子父子的任务完成后,一超同志到老隆,他又与连贯同志接上头,决定在老隆冠华旅店设立临时联络地点,派我与小郑(名不详,据说是连贯同志的女婿)为临时接待员。当时老隆镇是东江赴韶关转运点(广州沦陷后,伪省府设在韶关),我们接待的有华北银行经理邓文钊先生(后来是香港华商报名誉经理,解放后出任广东副省长)等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几十人。党组织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决定迅速隐蔽转移。谢一超同志即派我回兴宁,通过海丰进步商人,马拱先生,解决车辆运输。最后搞到了六部运盐汽车把这些民主人士及进步文化人迅速撤离老隆,安全送往韶关等地。
四二年四月底,连贯同志派一超同志到韶关(我随之行)在中山公园西边侨兴行与丘海山同志接头,并与乔冠华经常联系工作。四二年端阳后,日寇有侵入粵北之势,韶关大疏散,谢一超兄接通知,急返东江,但路途阻绝,况又病魔缠身,旅费又缺,我硬着头皮向乡亲借了百多元伪券,仅够他步行费用。我忍泪同他作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后来听说他到连平的灯塔地方,病已发作,大量吐血,后由蓝训材同志前往护送他回海丰。到汕尾后,他一病不起,四五年八月份,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却与世长辞!当时他才四十二岁。其爱人及子女后往香港,至今下落不明。一超同志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精明干练,有胆略,临危不惧,对事业競競业业,不辞劳苦,死而后已。柳亚子先生把他比作掩护伍子胥的“芦中人”;廖承志同志曾来信称他是一位“很能干的好干部”。然而这样的我党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竟然被人诬为“叛徒、反革命”,真是荒谬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