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脚蛇 于 2025-10-19 10:42 编辑
陈宝荣/原创
当莲花山的晨光点亮公平水库的粼粼波光,我总会想起沉睡水底的冷饭埔,想起那个遥远的墟市:公元806年的某个清晨,挑着潮州柑的船工与牵着赣南黄牛的畲民,在罗輋河沙溪口的卵石滩上完成第一笔交易——以斗斛丈量诚信,以秤杆称出公道。

一、公秤初悬:从石阶到神龛的契约
唐元和年间的赴墟,原是山海子民的生存默契。
当惠潮嘉三州的商旅沿着石阶踏露而来,海丰城正在沉睡。这个山海交汇的要津,藏着天然的公平:沙溪口的卵石平整如砥,可作量具;罗輋河的水纹恒久如一,堪为标尺。“公道平宜”的口碑,便在往来商贩间悄然传开。

直到一群士绅在庙前悬起第一杆公秤,将交易契约焚告神祗、刻进石器的纹路。“公平”二字自此从斗斛的豁口溢出,沿着罗輋河——古黄江的帆影,漂向远方的海港。 南宋末年的飓风,试图撕毁这份契约。元军的烽火烧进海丰,焚毁文山守护的城垣,公平墟的土墙也在洪水中倾颓。 虽易名“太平墟”祈求安康,却掩不住民间对“公斗”“公秤”的执念。

姚举人捐资修墙的次年,中了进士,远赴山东为官,他题写的灵符终究亦未镇住故土的水患。
直到那个建醮之日,当挑着腥鲜的投墟者被拒之门外,老林岗的招财爷忽显灵光——原来真正的墟市,不在官府的规矩界限里,而在百姓用脚步丈量的土地上。

二、罾地生墟:风水流转间的生存智慧
临时起意并非空穴来风,“𠾐吖𠾐,骑马去海丰”只是一种向往。清初的迁界令下,助虐如一把利剪,剪断了沿海居民的生计脐带。
就在界碑林立之时,石塘都莲丰乡的财主吴蒙正却带着地师廖宗明淌过狮仔岭,寻觅风水宝地。 几番踏勘,廖地师站在老林岗顶用客家话点破:此乃“罾地”,鱼入则亡——“鱼”者,“吴”也。这看似凶险的判词,实则暗藏“海纳百川”的玄机。
廖地师又道:在此建墟收租,建四大宫镇住“罾杆”,繁华可期。这是对杂姓共居的巧妙安排,契合着“和而不同”的古老智慧。

康熙十八年的锣鼓声中,新墟场日兴市确立。八音奏响的不仅是吉曲,更是山海货殖的交响;正字戏与白字戏的对台,宛如中原古韵与本土乡音的对话。
当石鼓潭的船民将妈祖像蒙上红布,请上龙船肚溪岸畔,他们完成的不仅是信仰的迁徙,更是对“水深则灵”的商业地理的重塑——那些沉在溪底的烤烟余烬,何尝不是旧墟涅槃的星火?

三、公义长流:从墟市到时代的潮音
雍正年间十二条街巷里,双合号的米香与永兴店的药酒,酝酿着市井的醇厚。四大古井的水纹中,沉淀着罗輋河千年不变的契约精神。

当嘉应州翰林李象元在布街兴建社学,他筑起的不只是青砖黛瓦,更是“耕读传家”的文化根基。 铁匠铺的锤声与织机的咔嗒,在嘉庆年间的晨昏里,升级为24街音符,合奏出早期工业的序曲……
这份公义,在二十世纪迸发新的光芒。当彭湃与万清味在平岗约的晒谷场举起农会旗帜,他们接过的不仅是先辈的秤杆,更是“天下为公”的精神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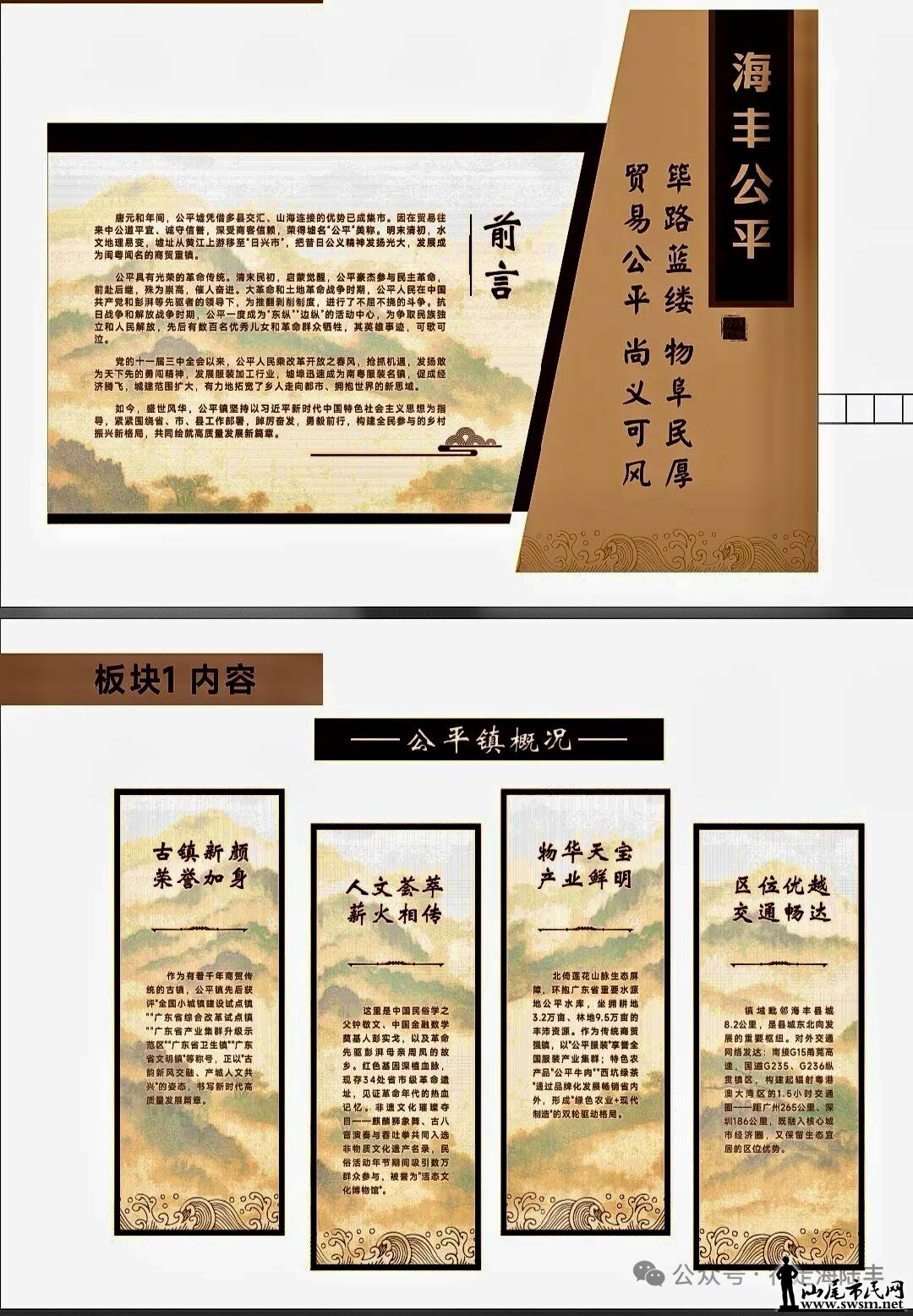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曾停泊妈宫码头的木船,化作缝纫机的针脚;昔日挑担叫卖的肩膊,变成流水线上的巧手——服装产业的崛起,何尝不是古老墟市精神的当代续写?
当机器轰鸣取代了墟日的喧哗,我们依然能在公平水库的坝上,听见罗輋河水千年的低语。站在妈宫码头旧址眺望清浅的河流,公平墟的故事仍在续写新的篇章。

那些刻在冷饭埔的记忆、量在斗斛里的诚信、融在风水中的公义,早已超越地理的界限,化作血脉中流淌的精神契约。而潮流改向,我们再次站上历史的码头抉择,仍要坚信公平墟不会消失,它只是从沙溪口的卵石滩,迁往了更广阔的人间……
妈祖广场的展馆里,那杆公秤依然悬着,称量着每个时代的良心与梦想。

附:公平墟场转换的原因分析 1. 原墟水患频仍,生存堪忧
古黄江上游罗輋河水势汹涌,屡发洪灾,公平老墟地势低洼,常受侵扰,难以承载大规模人口安居。
2. 河道淤塞,水运渐衰
泥沙不断淤积,航道日浅,舟楫难通,老墟赖以繁荣的水运优势不再,商贸往来受阻。
3. 康乾盛世,南迁拓新
适逢康乾时期,南迁人口涌入,新墟“日兴市”应运而生,渐成聚落,生机初现。
4. 迁界内徙,人口涌入
清廷迁界令下,沿海居民内迁至莲丰乡一带,新墟藉此迎来人口增长红利,奠定发展根基。
5. 妈宫码头与公信文化,促成繁荣
新筑的妈宫码头畅通水陆,加之“公道平宜”的市风传承,共同推动日兴市稳步壮大,终成一方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