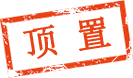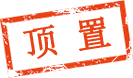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心无挂碍 于 2025-10-7 20:05 编辑
9.3阅兵的礼炮余音还在上空回荡,电视里红旗招展的画面尚未淡去,我却接到了她离世的消息。她闺蜜也是我的同学说:“她走时还在牵挂着你,还在念着你的名字,弄得她丈夫很尴尬,她那眉宇间凝着化不开的忧郁,像极了沙溪中学春天里,被细雨打湿的李花瓣。”听到这个噩耗,我只是播放当年她教我唱的《葬花吟》《雪中情》《追梦人》和潮剧《彩楼选婿》。当年的你,音容笑貌,举手投足,衣着服饰,仿佛在眼前。 总记得沙溪中学实习的日子,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实习生。清晨一起踏着露水去教室,傍晚顶着暮色写教案、批改作业。学生们围着我们喊“老师”,也许是第一次当老师,她的脸颊会泛起浅浅的红,含羞浅笑。 沙溪是潮州一个农村镇,校园外的田间小路纵横交错,暮春的稻田上面,萤火虫到处飞绕,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除了水稻花香,还有金黄的油菜花铺到天边。 工作之余,同学们在宿舍打牌聊天侃大山,我们静悄悄出去。憨厚的带队老师余老师的房间守在最前边,每次经过他的房门,他总是微笑着对我们说:“又要去晒月亮啦!注意安全,不要太晚!”一声“余老师好”,我拉着她的手,逃也似地漫步在田间小路上。有一次,晚风来急,她的白衬衫被风掀起一角,我伸手去扶,指尖触到她的手腕,惊得她像只小鹿般躲开,却又偷偷回头,眼里盛着星光,嘴里带着微甜。那一刻,两颗心就碰在一起了。 学生说:这里有个李古洞,很好玩,于是我们一起去爬李古洞。洞里潮湿的石壁沁着凉意,她怕黑,怕蛇,怕老鼠,也怕蟑螂,而洞里恰恰都有她所害怕的一切。一边跟着我走,一边紧紧地攥着我的衣角,生怕我飘出洞口离开了她。我转身牵住她的手,小心翼翼往前爬,爬到在没有光线的幽暗里,一块大石头挡住去路。我们只好停下来,环顾四周,黑压压的,有点吓人。 “怕吗?”我问她。“没有毒蛇吧?没有毒蛇就不怕!”她回答。但还是怕。她不经意中往我胸前挤,手很凉,还微颤着。黑暗中,无意中,两瓣唇碰在一起。第一次吻了她——那吻很轻很凉,带着山野间草木的清香,虽然叫走了黑暗与恐惧,但好像是一个易碎的梦。 她没有丝毫准备,无比珍贵的初吻就没了,很惊讶,脸色吓得很苍白,一路上她眼睛梨花带雨似地看着我——不眨眼地看着我,想确定我是真心还是轻浮,手也紧紧抓着我。我也很懊悔,没有给她一点准备的时间,就把她的初吻抢过去了。实在不应该。 实习结束那天,学生们哭着塞给我们纸条,送给我们小礼物、相片。她也很伤感,躲在教室后门抹眼泪,我拍着她的肩说:“学校的车在外面等我们,我们上车吧,以后会再见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声再见,难道就藏着我们命运的伏笔?难道真的有一语成谶的预言? 实习后还没有毕业,我们回到韩师,继续最后的毕业复习考试,但实习后,我们都人心浮动,浮躁不安,很少能静心去图书馆去教室读书复习了。为了不影响毕业考试成绩,我们约好:晚餐洗漱后,去教室学习两个小时,才能出去“拍拖”。 晚上十点后,我们常去韩文公祠。夜晚中的古祠很静,走廊的檐角的风铃轻轻响,我们十指相扣漫步沿着石级,走去上面。常常坐在一条石凳上,她靠在我肩头,总说要一辈子和我在一起。我们带着茶具,也去笔架山公园泡茶聊天,坐在空旷的山顶,有幕天席地的感觉,我们看着当空皓月,数着星星,当小城的街灯次第亮起来后,她指着最远的那盏灯,说想和我去远方,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简单的日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规划毕业后何去何从,毕业后的归宿我们谁都没有提起,好像是一片“盲区”,甚至有个早熟的叫莲的女同学还找我们,提醒毕业后要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我们居然对她的“远见”轻描淡写,当作耳边风。也许这是一种宿命吧:上辈子修道不够,留给我们的,只有爱恋、没有婚姻、家庭,只有那“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结局。 毕业那天,校车送我们毕业生回家。在校道上,她低着头,哭得像个泪人儿,一只手里攥着我送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另一只手紧紧抱着我的胳膊,久久不松开。那个镜头,感动了在场很多人,以至于多年后,师妹冬还对我提起那个场面,还遗憾地说:没想到你们最后没有走在一起,太可惜了! 当时我以为那是承诺,却忘了她是温室里长大的花,经不起风雨。她终究没能随我闯天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一张无形的网,将她困在了原地。其实,当年我也无脑:我干嘛不去汕头工作呢?如果去汕头,不也能在一起吗?叹只叹,之前的汕头大学是我的伤心地,我不想再看见汕大,所以毕业后本来有机会去汕头谋职,也只好“魂断汕头”。 我第一次去看她时,她带着我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去莱芜风景区:那是澄海区南部海滨的海滨风光区,那里有洁白沙滩、奇特礁石群,登上莱芜岛可俯瞰海湾美景。一路上,我牵着她的手,爬到一个小山坡,她眼睛好,环视一下周边,见没人,就把我的右手拉到她胸前,久久不放,眼神坚定不移地对我说:“无论发生什么,妾身这心这身子永远是夫君的。”“无论发生什么”是不是在暗示会发生什么呢?她连称呼都回到古代了。 第二次去看望她,她奉父母之命已经结婚了,丈夫是她父亲老战友的儿子——世交之情。原来满面红光、嘴唇红润,腿脚灵活、身子日渐丰盈饱满的她,却瘦了,穿着已经不合身的衣裳,眼里没了往日的光。她拉着我的手,脸靠在我肩膀,指尖冰凉,说“日子过得很闷”,却又摇头,“算了,就这样吧”。 我知道,她不是不想逃,是不敢——从小娇生惯养的她,从小唯父母之命是从的她,早已失去了冲破牢笼的勇气,也没有和我“白手起家”“共同创业”的意志力。 再后来,我们渐渐断了联系,只从友人处零星得知,她跟我分手之后,伤心欲绝,骑车走神,被三轮车撞倒了,车祸严重,腰椎骨折,是她父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请李嘉诚医院的骨科高手,才让她重新站立起来。她的日子过得平淡如水,甚至有些苦闷,却从没想过要改变。只是每逢在中秋节,把愁心与祈祷,寄予明月清风,祝福远方的人康乐。 白驹过隙,那些在沙溪中学的同甘共苦、李古洞的心跳、韩文公祠的缠绵,笔架山公园的诺言、莱芜山丘的托付……仿佛还在昨天,她却已走完了短暂的一生,但我不相信,我更相信是她闺蜜在说假话,因为我们约好退休后,要重走我们一起走过路过的地方。 此刻,窗外的风又起了,像极了沙溪中学那年的风。我想起她站在李树下的模样,想起她眼里的星光,想起她说“想和我去远方”。只是这一次,风再也吹不回那年春天,也吹不回那个敢爱却不敢挣脱的她。九月的风很凉,凉得像她最后凝在眉间的忧郁,一吹,就散了,只留下满地回忆,像那年落了一地的李花,轻轻一碰,全是碎掉的疼。 |